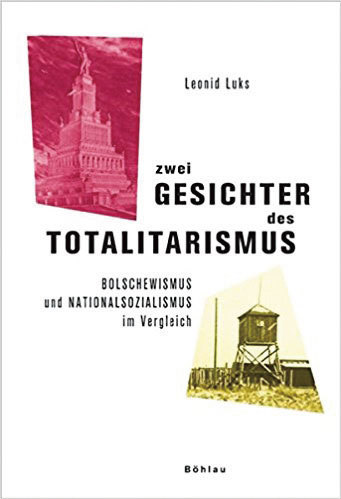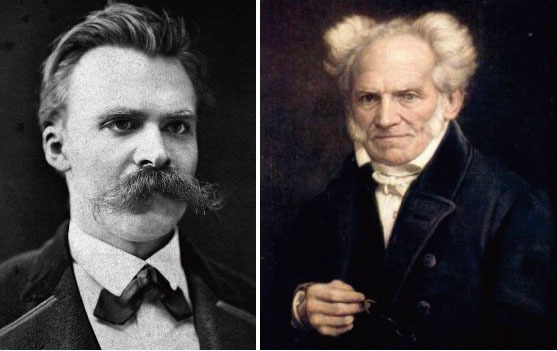「紅」字下的反人類罪——重發〈紅衛兵是如何誕生的〉一文按
我的〈清華附中紅衛兵誕生記〉寫於大約20年前,1996年,文化大革命30周年的時候。當時是在偶然的契機促使我決定寫該篇文章;因為一位到了德國的清華附中學生居然在文革30年後說了一些不著邊際,不屬實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及看法。那時的我在認識論的問題,思想方法方面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正在自己的思想領域上探究,這類歷史問題、回憶問題本來我是準備在思想工作,也就是問題的探討告一段落以後再來整理記述,但是由於那個刺激,並且也想到趁著記憶力還好,決定將一些東西先寫出來。
那篇文章因為內容都在腦子裡,所以寫來並不費力,只花了三四天的功夫。當然還因為我當時正在構思寫作另外一篇文章——關於鄧小平的所謂改革與極權主義專制的關係,也就是我那時提出了極權主義的兩種表現,教條的和實用主義的。後者我花費了更多心思,但是兩篇寫畢投出去後,第一篇〈清華附中紅衛兵誕生記〉引起的反響遠比後一篇我著力很多理論性的文章大得多。後者被劉曉波注意到,並且在1999年的文章中使用了我的觀點,當時我真的以為他對共產黨的看法及態度有了改變,在後來獨立筆會的選舉中把票投給了他。但是其後的發展讓我看到,詞句的接受不等於立場和處事態度有了根本的改變。
那篇關於紅衛兵誕生的文章當時甚至給某些刊物帶來長安紙貴,儘管如此有三點我心裡很清楚。
第一,在對極權主義的研究上,我還在路上,還有很多重要的問題等待我釐清;如極權主義的思想根源、文化根源,極權主義專制和傳統專制的區別,啟蒙是什麼?東西方的不同是什麼?二元與多元問題,馬克思主義繼承的是西方的什麼東西等。這就是此後我這十餘年的工作。
第二,伴隨我思想的進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尤其是對它在全球化、現代化的背景下,來自西方的根源的認識我會不斷探究下去。這也是18年後、今天的我的狀況,我已經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背景上,從上個世紀初期在西方,尤其是歐洲兩次大戰給社會和知識分子帶來的問題,從極權主義的產生帶來的文化問題上來研究這個極權主義的普遍現象在中國的特殊反映。
第三,就是這篇文章為周圍人帶來的新鮮和刺激我自己也是料到的。因為那是我從1970年以來,告別那個社會及其意識型態,尤其是文化的結果。儘管很多看過的人,乃至叫好的人大概沒有意識到這種思想和文化的距離,但是30年來的差距還是會讓很多人感覺到。所以我當時對朋友們說,這篇東西我雖然並不認為寫得很成熟,可20年內大概沒有人能夠寫出超過這篇的文字,也就是在思想的廣度和深度上能夠涵蓋住此文,並且給人更多的描述視角和思想啟發。事情發展也真的是很不幸,20年幾乎已經過去,我認為我的預言基本上成了現實。這其實毫不奇怪,猶如唱戲一樣,幾句簡單的唱詞,可唱好它的功夫卻是幾十年的努力。因為沒有人付出過我那樣的努力來告別那個社會,重新學會如何說話和描述。
從1969年開始,我為了認清並且說明我所參加過的文化大革命是怎麼回事,從馬列哲學的反省、反叛進入到英國的經驗主義哲學,自學了外語、物理、數學,其後又在大學和研究生繼續學習了物理,更不要說在文史上必須下的功夫。我在思想和歷史領域中的「音準」,首先是拋棄共產黨意識型態的「野狼嚎」,然後是一個音符一個音符地學習、練習而來的。
如此說法我的確有些放肆,因為借用了共產黨樣板戲中的語言,「野狼嚎」。可共產黨《人民日報》的語言,假大空、意識型態化的語言,比「野狼嚎」更為甚。這就是我對我的同學卜大華的弟弟,低我兩個年級校友卜偉華的文革史研究的看法——其知識框架和語言使用決定了其文革研究不過是文革繼續。我對卜偉華毫無個人恩怨,卜大華說一直對我不錯,這我也清楚,我點卜偉華的名字只是同情他而已;一個人居然搞了一輩子文化大革命,這從生命的角度看是很可悲的,可說是浪費了自己的生命,枉為人一場!
搞了一輩子文化大革命的當然絕對不是卜偉華,還有金觀濤們。不信你去分析他們的語言和概念,他們思索和談問題的角度和方法。至今金觀濤談文化大革命及他們那代人,談馬克思主義乃至阿倫特,居然依然完全用的是奧威爾《一九八四》中所說的新話和新思維!
我的另外一個校友閆陽生在看過我的這篇文章10年後,也寫了篇有關紅衛兵的文章。閆陽生大約是真心實意地不想再繼續文化大革命了。可惜他由於沒有認識論、方法論的變化,沒有一個更為廣闊的,或者說更為準確的參照系,他對文革的看法依然沒有跳出牢籠,摘掉那副60年代給他佩戴上的眼鏡。他以為從「反校領導」到肯定校領導就是翻天覆地的變化了,就是超脫出去看文化大革命了,殊不知他開始高度評價的清華附中校領導其實是文革的先鋒,他們在60年代在清華附中推行的一切,包括教改,都是文革的前奏曲,或者說都是一場大的、反傳統的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
當年的清華附中校領導,清華大學校領導與紅衛兵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
50年代開始的院校調整,教育革命,階級路線,推行又紅又專為紅衛兵的誕生奠立了基礎,創造了溫床。蔣南翔和萬邦如的黨團支部與紅衛兵的區別不過是希特勒的納粹黨和黨衛軍(Die
Waffen Schutzstaffel,簡稱Waffen-SS)的區別。小巫見大巫!
我曾經感嘆過命運捉弄人,因為那位張承志想出來的「紅衛兵」與「黨衛軍」簡直是天造地設。就憑這個名字就毋須多費筆墨揭露紅衛兵了。只要一說到「紅衛兵」三字,正常的人就會立即想到「黨衛軍」這三個字!而這就牢牢把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因為黨衛軍是希特勒專門屠殺不同族群的核心暴力組織,而紅衛兵的成立首先就是專門執行階級路線,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正是因為他們感到蔣南翔和萬邦儒們在階級路線上還不夠純粹,不夠殘暴,所以才有了紅衛兵。
閆陽生溫情脈脈的回憶意味著他的什麼問題呢?我想如果他善良,他自己應該會去想。他只要明白,不再想用野狼嚎
的腔調來談文化大革命不只是輕聲細語問題,因為只要概念和方法沒變,音調就沒有根本改變。而這就進一步意味著要寫文化大革命,要看清、反省文化大革命就首先要反叛,拋棄文化大革命給我們的一切。「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道理再簡單不過了!
沒有反叛,不改變自己的價值和倫理標準,不改變自己的說話方式,也就是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談文化大革命談不出任何新意,或者說談不出任何真正有價值的內容來。
為此,時下陳小魯和宋彬彬的所謂「道歉」,人們首先要問的就是要反省道歉的是什麼?
對「反省道歉」來說,最重要的是你們從懂事起就跟著推波助瀾,大力推進的階級鬥爭,階級路線,無產階級專政。那是貨真價實的「族群滅絕」。你們那個時候並沒有把地富反壞右,乃至他們的子女當作人看。你可能真的沒有直接打卞仲耘、沈寧(陳小魯的同校同學),可你們始終積極推動的是對他們的踐踏和暴力。取消高考、破四舊、成立紅衛兵,哪一件事情不是如此呢!你們什麼時候覺得那些平民的命,「地富反壞右」的「命」是「命」呢?就是現在不也是依然如此嗎!你們覺得那些有自己信仰的人,藏族、維吾爾族民眾的命,那些不接受一黨專制的人的命是命嗎?
所以反省和道歉本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可對宋彬彬們又是一件非常難的事。就如寫文化大革命,寫紅衛兵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卻也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正為此,20年後,我覺得我的那篇20年前的文章,〈清華附中紅衛兵誕生記〉還是沒有過時。
所以,最根本的一點是,沒有對自己以往的顛覆和反叛,道歉是虛偽的;而真誠的道歉則一定導致顛覆和反叛。因為人,只有到了他深切地體會到任何人的尊嚴都是不可觸動的,任何人的命都是一樣的時候,才會有真正的反省。這不僅是西方所談的普世價值,也是我們民族的傳統倫理。用我們倫理觀說,就是接受「四海之內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教無類」,而這只有放棄一黨之私才會有新的視角,新的開始。
文革始自階級路線、族群滅絕、一黨一己的專制,紅二代的反省和道歉和整個歷史的反省一樣,首先就應該是對那個「紅」字下面的反人類罪的罪惡的反省與摒棄。捨此都是自欺欺人!◇
|
|